英雄联盟投注 yingxionglianmengtouzhu 分类>>
走火:萨拉热窝事件与通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曲折道路英雄联盟投注官网- 英雄联盟投注中心- 下注盘口
英雄联盟投注官网,英雄联盟投注中心,英雄联盟下注盘口事实上,皇帝为期三天的波斯尼亚之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程表塞得满满当当,包括国事接待、军队检阅,以及与波斯尼亚多个宗教民族社区——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犹太人——的领导人会面。在穿过黑塞哥维那回国的路上,弗朗茨·约瑟夫甚至还抽空欣赏了莫斯塔尔(Mostar)的古桥,这座不朽的地标是该国先前的统治者奥斯曼土耳其人在 16世纪建造的。据说这位79岁的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在他最南端的斯拉夫领地过得非常愉快,以至于一度对他的东道主、波斯尼亚总督马里扬·瓦雷沙宁(Marijan Varešanin)将军大声说:“我向您保证,这次出行使我年轻了20岁!”
事实上,他的生命险些提前6年多结束。比起4年后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和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对波斯尼亚那次名气大得多的访问,以及在萨拉热窝的,这次的安保要严格得多。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名叫波格丹·热拉伊奇(Bogdan Žerajić)的武装民族主义者悄悄靠近了皇帝陛下。有两次,这位波斯尼亚学生离光彩夺目的皇帝已经如此之近,以至于他沮丧地对一位朋友吐露道:“我差点儿就碰到他了。”可是热拉伊奇没能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勃朗宁手枪。反倒是在6月15日那天,或许半是出于个人的痛苦、半是出于爱国的热情,这位24岁的年轻人在瓦雷沙宁离开刚刚举行了开幕典礼的萨拉热窝议会时,向他开了5枪,全都差之毫厘。他的最后一枪倒是很准,打碎了自己的头盖骨,于是他成了波斯尼亚人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争取自由的烈士形象。
19岁的波斯尼亚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曾经在热拉伊奇墓前立誓复仇,但与他心目的英雄不同,普林西普进入皇储弗朗茨·斐迪南的近距离射程时,并没有惊慌失措。然而他差点儿就失去了机会。1914年6月2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整个欧洲都被习惯性地描述为“晴朗无云”“无忧无虑”“一片祥和”和“完美无瑕”——普林西普潜伏在大公路线上的人群中,就在这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划破了这一场面。在远处的阿佩尔码头(Appel Quay)路,普林西普的同谋者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Nedeljko Čabrinović)向载有弗朗茨·斐迪南及其妻子霍恩贝格女公爵(Duchess of Hohenberg)的汽车投掷了一颗炸弹。一些旁观者把炸弹声错听成了皇室成员入城时的礼炮轰鸣声。然而,普林西普并不确定大公是否还活着。敞篷汽车里继承人考究的头饰上突出的绿色羽毛从他身边掠过后,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弗朗茨·斐迪南从当天萨拉热窝的一次暗杀行动中死里逃生。此时,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甚至没有开过一枪。
查布里诺维奇很快被捕,而其余的刺客也都退缩了,或者干脆逃走了。普林西普是个例外。他没有溜进人群、匆匆出城,而是直接在码头对面的街角二次就位,就在莫里茨·席勒(Moritz Schiller)的熟食店前面。讽刺的是,这条路在那个转角拐入的街,叫作弗朗茨·约瑟夫街。但这位意志坚决的刺客并没有停下来吃三明治。皇室路线得到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因此普林西普知道,在市政厅举行正式的欢迎会后,车队会在这里驶离阿佩尔码头,进入萨拉热窝市中心。果不其然,前两辆汽车确实在那里转弯了,后面跟着载有弗朗茨·斐迪南的那辆。然后,计划外的某件事情突然发生了:座位离大公最近的波斯尼亚总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 Potiorek)将军喊道:“哎呀,你走错路了!”司机利奥波德·洛伊卡(Leopold Lojka)听从了他“调头”的命令,踩下了刹车。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听从了自己的良心,拔出了勃朗宁手枪。只是他瞄准的不是移动靶,而是面前坐着的活靶子,佩戴着华丽的绿色羽毛。
历史爱好者们对这次“错误”的转向大书特书。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查布里诺维奇的那次尝试,那么当皇室一行人聚集在市政厅时,波蒂奥雷克就不会改变行程路线,避开市中心的狭窄街道,改为沿阿佩尔码头直接前往驻军医院,探望在爆炸中受伤的那位副官。如果他没有修改路线,那么当大公的汽车按照最初的计划,无意中拐到弗朗茨·约瑟夫街时,洛伊卡就不会奉命改变行车路线。如果他没有在那个转角处停车,那么普林西普可能会射偏,或者仅仅是打伤大公——距离这么近,他的第一颗子弹还都只是打穿了车体,不经意间杀死了女公爵。或者,在推推搡搡的人群中,这个身材矮小的刺客可能根本连枪都开不了。如果发生了以上任何一种情况,自那个“晴空万里”的夏季星期天以来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都可能会被改写,而那一天也标志着一个同样晴朗的时代——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的结束。无论如何,世界大战都不可能在一个月后爆发。
可供选择的结果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也是极其耐人寻味的。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波格丹·热拉伊奇虽然无人问津,但他没能射杀弗朗茨·约瑟夫这件事情本身,却和4年后那次传奇的“错误”转向一样,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毕竟,如果奥匈帝国(二元君主国)皇帝被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在1910年登上皇位会发生什么,又有谁能说得清呢?或者同理,如果弗朗茨·约瑟夫在1853年2月——他侄子出生的10多年前——被杀害,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彼时,一名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用匕首刺中了他的脖子,是坚硬的军装衣领、一位动作迅捷的爱尔兰伯爵和一位路人屠夫的奇异组合救了皇帝的命。也不是每一个历史转折点都如此戏剧化。1914年4月,83岁的皇帝得了肺炎,病得很重。维也纳的佣人们片刻不离地看护,弗朗茨·斐迪南在科诺皮什切城堡(Konopiště)(波希米亚)的马车随时准备载着他向首都飞奔,以便迅速举行加冕礼。如果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没有挺过来,新登基的皇帝就不太可能去波斯尼亚检阅部队,他完全可以派和蔼可亲的侄子卡尔(Karl)去。还有,冲着弗朗茨·斐迪南那强硬、独裁的脾性,匈牙利人可能已经造反了。又或者,作为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他可能会把那年夏天的军事演习从酷热的波斯尼亚改在他心爱的波希米亚进行,因为大公很担心南方的酷暑,几乎从一开始就不会去萨拉热窝。
本书并不是要涉足充满危险、无边无垠的反事实(“或然”)历史雷区,纵使它经常给人以启发。本书也不会冒昧将波格丹·热拉伊奇这个不那么知名的人物抬升到加夫里洛·普林西普那样的传奇地位,后者被称为“史上最著名的杀人凶手”“引发世界大战的男学生”“20世纪最重要的人”,以及“改变这个世纪的人”。的确,有太多太多的历史解释,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1 000万人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崛起、欧洲衰落、南斯拉夫垮台的一切,以及作为过去一个世纪缩影的所有惨剧和暴行,都归咎于普林西普的“几颗子弹”。相反,这部关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作品,是将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的枪声置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仔细审查这种修辞构式和其他常见的不严谨之处。它要问的是:普林西普的枪击最初以何种方式变得如此传奇,又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凸显出来,就触及了一个问题的实质,即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经常是如何被描写和加工处理、叙述和回收利用的。例如,记者们把当代的每一场惨案都渲染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12学者们把对这位皇位继承人的谋杀与当今的大肆杀戮画上等号;学术专著和奥地利的纪念碑宣称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的受害者”;教科书教导我们,普林西普在欧洲“火药桶”(“有暴力倾向”的巴尔干地区)“偶然”开了枪,于是就粉碎了各个帝国;而这位波斯尼亚塞族刺客也被诋毁成“塞尔维亚狂徒”,还被编排成在现代历史决定性的“闪光灯时刻”吃着三明治。此时,我们对这段冷酷的历史是否获得了更强大的洞察力呢?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类司空见惯的概念是否在妨碍我们将这场政治谋杀放到适当的背景中加以研究,借此来操纵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呢?
我们可以对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提出这类问题。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出于这样一种感觉: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已经进入了神话领域。我并不是在通常的历史意义上狭义地使用这个词,即有选择性地叙述过去,使其对生活在当下的特定集体产生特定的意义。对许多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塞族人来说,情况确实是这样。他们把这场政治谋杀神话化,视其为将南斯拉夫人从奥匈帝国解放出来的英勇行为。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萨拉热窝事件”之所以能够引发被“神话”一词充分唤起的普遍共鸣,是因为它在20世纪一直明晃晃地笼罩在人们心头,却没有被完全理解,恰似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争论本身,永远都不会平息。这场政治谋杀被神话化,是通过夸大那些差点使它落空的“随机”因素;把它变成一个由“充斥着暴力”的巴尔干地区“躲在暗处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团体”和“国家赞助的”策划的复杂阴谋;用反事实的臆测将它淹没;轻轻松松地把普林西普的三明治和刺客们身患绝症(肺结核)等彻头彻尾的杜撰并入其中;利用它来与当今的灾难做现成的类比;用“偶然”和“命运”这类陈词滥调,以及“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暗杀”等夸张的习惯用语,来淡化那令人惋惜的结果——“差点儿就失败了”,一位学者认真地讲述道。正是“震撼世界的枪击”和“闪光灯事件”这类措辞——事情刚刚过去时,其实只产生了有限且短暂的国际影响——使“萨拉热窝事件”具有了神话所特有的那种无忧无虑的朴素和“无比幸福的明晰”。在人们的想象中,波斯尼亚和整个欧洲的天气,在 1914年6月28日——甚至是纵贯欧洲的“最后一个夏天”——都是极好的,这就是一个很贴切的例子,因为它营造出了美好时代的一切都明媚宜人的错觉。可就在这时,某个来自“落后”(“巴尔干”)国家、“有些疯疯癫癫的塞尔维亚少年”,仿佛晴天霹雳般突然冒了出来,即刻使人类堕入冰冷的黑暗。或者正如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后来的叹惋:“转瞬之间”,这个安全的世界就“像一个中空的黏土容器一样,碎成了无数片”。
萨拉热窝暗杀事件是现代历史上一场颇具戏剧性的事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然而,想要把它讲述得扣人心弦,并不需要戏剧化的渲染。本书并没有开创任何新的方法论,只是将1914年6月28日的事件嵌入其复杂的长期背景。《走火》将暗杀事件置于人类经验的广域内,既不是在推翻历史准则,也不是在指责历史学家。相反,正如书名所示,这部作品的主旨是重新审视一个已经被阐述太多的著名行为——从事情在何时何地怎样发生,到谁是幕后黑手,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以及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也已经是好几种神话诠释的对象了,包括凶残的、英勇的自由斗士、堕落的罪犯、流行文化符号和“后青春期小流氓”。而他在塞尔维亚的所谓武器供应者,已经变成了这个“史诗级”阴谋的实际煽动者——“极端民族主义”“秘密”社团黑手会的“狂热[塞族]”。
至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自然背景,欧洲“危险的”巴尔干边陲,似乎永远无法摆脱对其原始、凶暴、任性本质的刻板印象。 20世纪 30年代,美国记者约翰·根室(John Gunther)认定,“巴尔干半岛上这些狭隘、穷苦、寒酸、凋敝的小国,可以吵出引发世界大战的架来,而且也确实做到了,这是对人类和政治本性的公然冒犯,简直天理难容”。对于这个“荒芜贫瘠”“灰尘弥漫”的地区“巴尔干人的野蛮”“东方人的怠惰”“信仰异教的塞族游牧民”和“发动战争的强烈嗜好”,其他许多作家也表示了不屑。1935年,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和政客写道,对于“文明欧洲”的这块“蛮荒之地”,除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致命火花,还能指望什么?将近80年后,另一位学者将这次谋杀描述为“奥匈帝国穷乡僻壤的一个偶然事件”。
和气候变化残酷无情的猛攻一样,1914年的全球危机并非偶然出现在巴尔干地区某处幽暗的“穷乡僻壤”,不为政治精英所察觉和关心。中欧强国哈布斯堡帝国在1878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攫取了管理权后,便直接参与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开发。当二元君主国于 1908年吞并该领地时,这片以萨拉热窝为首府的帝国领土(Reichsland)不仅引出了许许多多的暗杀阴谋,还引发了战前欧洲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之一。274年后,巴尔干战争使欧洲列强与冲突近在咫尺,以至于英国周刊《笨拙》(Punch)把它们的领导人描绘成正在试图压住“巴尔干问题”这口沸锅的盖子。尽管人们一直怀着这样一种印象,认为这是某个荒凉、偏远、衰退的国度一场自发的谋杀,但波斯尼亚是一个地缘政治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难题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而且严重到足以拥有一个专门的名称——东方问题,或者说,长期以来由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又名“欧洲病夫”)控制的欧洲土地,会变成什么样子?
东方问题对本书的历史叙事至关重要,但对于其他的政治势力,以及在世界变化最大的时代之一塑造了它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变迁,本书也都没有轻描淡写。法国诗人夏尔·贝玑( Charles Péguy)在 1910年指出,“文明世界在过去30年里的变化,比自耶稣基督时代以来的变化还要大”。学者们一致赞同这一点。“变化是生命的法则,大多数时代都是变革的时代,”文化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承认,“但是在 19世纪,变化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它比过去更加迅速,更加难以抗拒”。因此,本书第一章专门介绍了在“痛苦与不幸巨大、黑暗的地平线”降临欧洲之前的那个时代宽广的弧线。
出于同样的原因,6月 28日之后那段夹在中间且极其重要的时期,也在最后一章中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在许多叙事中,这次暗杀事件被表示为一场酝酿已久的战争的“火花”或者“导火索”。一旦对围绕萨拉热窝事件的所有内在阴谋、行动和谜团进行了详细彻底的考察,即使有的话,这些作品也很少会去关注六月谋杀案之后的七月[外交]危机这段决定性的历史了。然而,近些年来,对“改变世界的一个月”的几份严谨调查再次表明,在质疑这场战争的复杂起源时,过度的决定论会有怎样的危险。如果作者们要追踪普林西普慷慨激昂的心态,以至于跟随他的脚步在波斯尼亚艰难跋涉,连他的成绩单都要挖出来;如果弗朗茨·斐迪南幸福美满的婚姻可以被渲染成“改变世界的罗曼史”;如果记者们可以将大公遇害与从佛罗里达夜店大屠杀到俄罗斯武力控制克里米亚的所有事件相比较;如果学者们可以将萨拉热窝事件类比为“9·11”事件,那么,调查真正的决策者们各不相同的信念,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在那场所谓“改变了一切”的暴行之后,欧洲是多么接近于不开战。这位赤贫如洗的刺客不经意间引发了一场国际危机,但点燃这个著名“火药桶”的,却是一群光鲜亮丽、大权在握的政治家。
再者,这些人生活的时代本就充斥着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宣传”,以及其他要取人性命的民众抗议形式。所以说,大公的横死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除了事情发生时的地缘政治背景。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在亚伯拉罕·林肯遇害后说的那句“暗杀从未改变过世界历史”,放在萨拉热窝事件上听起来纵然可笑,但事实是,战争的决定并不是为了给弗朗茨·斐迪南报仇。尽管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无辜的城市,盛满了诅咒!……骇人听闻的灾难套上了忧郁的外壳”)和美国作家埃德蒙·斯蒂尔曼(Edmund Stillman,“一个时代为何要葬送在此地?”)等人愁肠满腹,但这些决定并不是在“凄凉”的波斯尼亚首府做出的。必须强调的是,世界大战和奥匈帝国后来的解体也并非“必然”。千钧一发的并不只有这次暗杀事件,还有许多可能改变战争结果的战役。
用著名哈布斯堡研究专家罗伯特·卡恩( Robert Kann)的话说,这一事件使“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那场遍及全球的战争,许多作家根本不会花这么大工夫来阐释这一事件。罪责问题——哪个团体或哪(些)个人发起并筹划了历史上的“完美政治谋杀”——是研究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核心问题,这也不难理解。它也在乞求一个引人入胜的答案——至少要对得起那套勾魂的话术,说什么普林西普开枪颠覆了世界历史的一切。然而,就像普遍意义上的战争起源一样,很难说清楚到底是谁煽动了这场阴谋,遑论他们的动机。
至于1914年6月28日之后的情况,我们可以说的是:金融市场仍然风平浪静;令人伤感的讣告很快便让位于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危机和法国的激情犯罪案等如火如荼的议题;甚至在奥地利首都,也有一份主要报纸将公众对这场政治谋杀的反应描述为“一种麻痹”,而不是“强烈抗议”,同时还有一些人指出,“冷漠”盖过了忧虑。萨拉热窝事件更像是一个悲伤的大标题,而不是即将到来的时代惊心动魄的预告片。或者正如一部专著的作者主张的那样:“与易燃物中的火花不同,谋杀本身并没有引发任何事情。”
随着斯蒂芬·茨威格所谓“太平的黄金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欧洲人继续过着暑假,其中许多人身处不久后将与之交战的国家。然而,政治家们却在焦急地等待着维也纳的反应。他们等来等去,一直等到大多数人都以为事情已经翻篇了,就像之前的那些国际危机一样。直到 7月 23日,大公遇害将近4个星期后,哈布斯堡君主国向塞尔维亚王国发出了那封充满挑衅意味的最后通牒,人们才从中感受到了剧烈的震颤。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寻求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一个大塞尔维亚(或南斯拉夫)国家,可能还要加上奥匈帝国其他的南斯拉夫地区。这份最后通牒在谋杀案发生后的几天之内就拟定好了,根本没打算让对方接受,因为维也纳早就决定对塞尔维亚动武了。
当然,二元君主国也做出了应尽的努力,尽最大程度、尽可能迅速地调查了谋杀案。然而,调查结果却不清不楚:武器由一名塞尔维亚军官和政府雇员提供;一些武器是由塞尔维亚批准制造的;波斯尼亚阴谋者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获得了武器,并被教导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在塞尔维亚海关和军事情报官员的非法协助下越境到了波斯尼亚。除此之外,正如奥匈帝国调查负责人 7月 13日从萨拉热窝发往维也纳的电报所言,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将塞尔维亚官方与暗杀阴谋联系在一起。如果在七月危机期间出现了这样一份铁证,那么俄国就不可能支持一个弑君的“流氓政权”,哈布斯堡帝国则会得到其武装部队首领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盼望已久的战争:在巴尔干局部地区痛揍一个民族国家。这个国家似乎铁了心要分裂二元君主国,将其南斯拉夫民族(必定有塞族人和波斯尼亚人,但也可能有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纳入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塞尔维亚(或南斯拉夫)国家。这样一场所谓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紧跟在新生的巴尔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在1912年/1913年打的前两次战争之后——对奥匈帝国来说可能并不好打。虽然塞尔维亚体量较小,资源也比较匮乏,但它的军队训练有素、久经沙场。尽管如此,如果其他大国置身事外的话,这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冲突。
可这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大战”,最常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持续了4年多的时间,跨越了 6个大洲,1 0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使最初的交战国悉数破产,推翻了三个欧洲王朝(以及此后不久的奥斯曼帝国),并在敌意未消、旧账未了的气氛中结束,直到1945年规模更大、死伤更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得以解决。一切皆因将塞尔维亚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既没有薄弱到让哈布斯堡帝国在强大的德国盟友的支持下咽下这口气,不去对身边的塞尔维亚小刺头动武;也没有充分到让俄国去冒险,任由自己的巴尔干伙伴被打服,甚至可能被彻底抹去。剩下的事情,则由欧洲“纠结的联盟”体系、列强的计谋和动员时间表来解决。
关于“萨拉热窝事件”如何催生这场剧变的总结,我们将在下文中对其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然而,无论要对实际阴谋负责的人是谁——无论是“患了肺痨”的“青少年”,“秘密”“恐怖组织”黑手会的“狂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还是其他某个隐秘的团体(阴谋论者所说的者、共济会、德国特工、哈布斯堡颠覆分子等)——要对大战负责的,却是欧洲列强的领导人。思索萨拉热窝的那次“错误”转向,可能在道德上令人安心,在精神上令人愉悦,但洛伊卡很可能从未踏足球场广场( Ballhausplatz)、威廉大街(Wilhelmstraße)、歌手桥(Chorister’s Bridge)、奥赛码头(Quai d’Orsay)或白厅(Whitehall)。而历史上的这次错误转向,正是在这些地方做出的。
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之所以在历史上凸显出来,是因为生活在所谓欧洲文明地区而不是“血流成河”的巴尔干地区的人所采取的行动。如果他们注意到了明晃晃的危险,并放下他们严守的原则,那么这个历史上“最悲惨的新闻报道”,在一个碰巧充斥着政治谋杀的时代,也只不过是又一场平平无奇的政治谋杀。弗朗茨·斐迪南可能不会经常被引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的受害者”,而是因其王朝价值观和政治智慧被后人铭记。普林西普也可能不会把脚印印在那个“开启了20世纪的街角”,而是成为20世纪历史的一个注脚。一种常用的表达,比如说萨拉热窝事件“大概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就充分说明了我们是如何对待这段惨痛历史的。换句话说,明明是欧洲的领导精英在世界历史上的走火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为什么普林西普的精确射击却被神话化到了如此程度?
一个原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只是一个瞬间——“啪”的一声,“砰”的一下,突然一击,正中要害。这里的要害既是象征意义上的,也是字面意义上的,因为子弹正好击中大公的颈静脉。再者,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既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又完全不按套路来。毕竟例行警告满天飞,因为在独立意识越发强烈的南斯拉夫人问题上,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王国的紧张关系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君主国的一些军事将领主张对这个暴发户国家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鉴于当地相当一部分人的民族主义精神,经常有人劝弗朗茨·斐迪南不要进行这次波斯尼亚之旅。他也十分清楚,皇帝曾在1910年与热拉伊奇的勃朗宁手枪带来的死亡擦肩而过。
但弗朗茨·斐迪南无法拒绝这个场合,理由事后看起来非常鲁莽,只有考虑到他成长的那个骑士时代才能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波斯尼亚之行可能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和贵庶通婚(还经常被诋毁)的妻子在帝国一起公开露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高傲的姿态,针对不断挑衅的、自巴尔干战争以来还扩张了版图的塞尔维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体面和“打肿脸充胖子”如此重要,大公不愿让他的东道主、总督波蒂奥雷克将军失望。最重要的是,作为奥匈帝国武装部队的总监察长,弗朗茨·斐迪南检阅一年一度的军队演习,之后与当地领导人一起公开露面,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大公才会罔顾警告,奔赴波斯尼亚,乘坐敞篷汽车穿行在首府。而那一天恰恰是塞尔维亚东正教的神圣节日圣维特日(Vidovdan),也是1389年塞尔维亚与奥斯曼土耳其人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的周年纪念日。弗朗茨·斐迪南与现实脱节,不懂礼节,执拗地相信他的天主教信仰,而不是稳妥的安保机构。他为了行事光明磊落,让自己和妻子陷入了致命的危险。
然而,他差点儿就带着完好无损的骄傲和人身安然度过了。那天在萨拉热窝的7个阴谋者是彻头彻尾的业余选手,最近才学会开枪或者引燃手榴弹。在第一个刺客没能行动、查布里诺维奇的炸弹也没能击中目标之后,随行人员本应得到长久的缓刑。他们聚集在市政厅,很快便取消了官方仪式,转而讨论是完全放弃当天的计划,还是采取其他不那么激烈的措施来保证皇室夫妇的安全。在阿佩尔码头继续行驶、避免拐进市中心的计划,差不多就是可以决定的与原计划偏差最小的选择了。然而,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实施,大公和他的妻子几乎肯定能活着离开萨拉热窝。当然,暗杀事件被神话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竟然真的发生了。
正是这种讽刺,使“萨拉热窝事件”如此富有神话色彩。一个不幸的事实是,结果证明,这颗漫无目标的子弹对奥地利继承人来说,并非不要紧。另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是,这个随随便便的一次性事件预示着后面的灭顶之灾。这里的讽刺指的是后者。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在他的经典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中写道:“每一场战争都构成了一种情境反讽,因为它的手段与预期的目的不相称到了耸人听闻的程度。”历史上的事情,无论是战争还是别的什么,还有比大公遇刺颇具讽刺意味的最终结果更符合这一表述的吗?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致命、最具破坏性、被一些学者称为“没有必要”的战争;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交战,开启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热战与冷战、种族灭绝与种族清洗、法西斯主义、毁灭、复仇,以及这一切所造就的尸骸和道德残骸。历史学家杰伊·温特(Jay Winter)和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断言,这场冲突构成了“一个短暂而野蛮的世纪真正的基础”。然而,自从奥匈帝国1914年7月28日开始炮击塞尔维亚,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也跟着匆匆加入战局以来,人们就一直对这场战争的原因津津乐道。
20世纪 70年代,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写道,他“开始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剧变”。弗朗茨·斐迪南·卡尔·路德维希·约瑟夫·马利亚·冯·哈布斯堡—洛林—埃斯特大公是一个“近乎偏执狂的人物”,不受自己国家的宫廷高层待见,与本国各族人民也很疏远。一个“夏季晴朗的星期天早晨”,他被一个“患有肺结核”“头脑混沌”的“塞尔维亚极端分子”(“乌合之众团体”青年波斯尼亚及其“秘密的”极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外围团体、臭名昭著的黑手会的“”成员)在一个“满是泥泞的原始[巴尔干]村庄”暗杀。继承人的汽车转“错”了方向后,极端分子偶然发现自己处在正确的十字路口、正确的毫秒时刻,一边还吃着三明治。发生了这样一场重大的人为灾难,可能是因为这个吗?
当然不可能。这场传奇谋杀案的后果,是诱发了一场没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外交危机,而自那以后,我们一直在努力接受萨拉热窝事件荒谬的后续。虽然所有这些努力产生了许许多多扣人心弦的解释、引人入胜的夸张说法,以及对“欧洲的命运”和“最后的星期天”浩如烟海(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文学反思,却没有产生一本基础深厚的历史书。这样一本历史书,还要考虑暗杀事件在历史上是如何被描绘的,以及这对于这段历史如何被普遍接受又有何意义。这本关于此次政治谋杀的书,目的正在于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将叙事嵌入其复杂的历史背景。第一章对战前时代进行了全方面的概述,之后的第二章聚焦于暗杀事件的主角——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和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以及他们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第三章的标题是“针锋相对的愿景”,考量了这些重要的巴尔干民族和地区——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哈布斯堡王朝——是如何在越来越危险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就各自立场进行谈判的。第四章讨论了富有争议的暗杀阴谋本身,第五章描述了1914年 6月28日的事件及其不断恶化的后果。对学者来说,这大概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故事。然而,去掉神话的成分,它仍然是一个深刻的悲剧,完全值得重新讲述一次。
本书是一部关于萨拉热窝事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著作。对于上述话题的研究文献已足够多,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巴尔干地区的角度重新叙述了这一问题,并综合了最新历史学研究成果。作者没有把重点放在普林西普的暗杀行动上,也没有强化围绕这一行动产生的观点,而是把这一事件嵌入巴尔干地区引起政治谋杀的复杂背景。因此,他阐明了20世纪初波斯尼亚危机和巴尔干战争在欧洲权力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解释了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哈布斯堡领导人如何在日益危险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谈判他们的立场。作者展示了这场刺杀是如何演变成欧洲政治家们无法和平解决的外交危机的。本书表明,对战争爆发负有责任的人不是暗杀者,而是首相、外交部长和将军。本书采用了大量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回忆录等历史档案材料,语言生动,历史细节丰富,可读性较强,也是对关于一战研究的文献的重要补充,为讨论萨拉热窝事件后的外交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新的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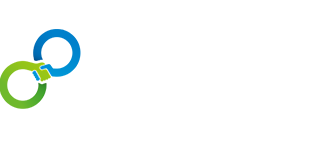
 2025-07-03 16:58:39
2025-07-03 16:58:39 浏览次数: 次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





